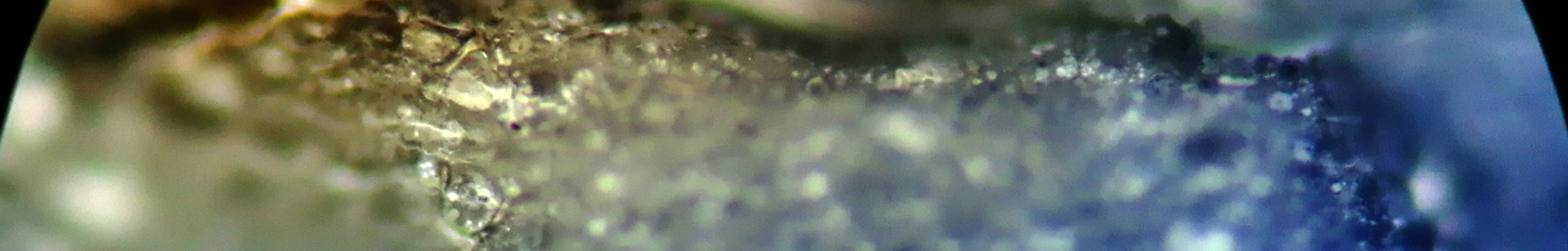总览
因此,梦想不是精神的虚空。它更是那感受到心灵充实的、时刻所赐予的礼物。(P83)
如果要给这本书做个定位,我觉得这是一套能够缓解人类当代精神问题的理论。
在远古时代,人类曾对宇宙和自然进行梦想,创造出了神话与宗教,将人类自己与世界融为一体:一切的自然都是围绕着人展开的,天为父、地为母,亦或者天地是人形的神所化成,因而人是世界的孩子,世界是人的梦想。通过这种梦想,人类以诗意在世界上扎根,找到了自己的存在之所,获得内心的安稳。而到了当代,科学与工业在破除迷信的同时,也把人与世界的感性连接一并破除了。日心说打破了地心说,也逐渐让人类意识到,自己并非世界的中心与原因,世界的形象变得冷漠。科学精神出现,工业革命爆发,人前赴后继地加入工厂与写字楼,在一切都加速发展的世界里,理性、效率、解决、策划成为了人人都应该拥有的优秀品质及能力。
在功利、理性与实用导向的气氛中,滚滚前行的人类社会将所有人都绑上了车轮,一切人都应当成为理性且高执行力的螺丝钉,以便让人类文明继续高速甚至加速前进。哭泣与白日梦只留给孩童,在成年人身上成了需要修剪的侧枝;感性更是软弱的标志,在网上与人辩论,若是“破防”便是“输了”。当坚强成为模板,当高执行力成为榜样、理性受追捧而感性被唾弃时,人也逐渐失去与世界的连接。
加斯东·巴什拉本人在大学取得了哲学及数学双学科毕业文凭,因此他的确很有资格来同时讨论科学精神与心理及哲学,也很有希望提出调和二者的方法。他的作品主要围绕着认识论与诗学两个论题提供理论,以现象学将二者串联。《梦想的诗学》强调了梦想的重要性,为梦想正名:白日梦并非某种“无用而丢脸的东西”,而是富有诗意的、稳定人类心灵的、令人获得平静的行为,可以成为、也应该成为人们主动去做的活动。
1960年的巴什拉写下了这套理论:每个人之中都存在着Animus与Anima两部分。除了为生存所需的、理性而阳刚的Animus,人之中还存在着阴性的Anima,而一切的安宁都是属于Anima的。阳性带不来安宁,安宁只能从阴性中求得。人应当主动梦想,以梦想来获得内心的阴性安宁。
这本书是我从上半年出差期间开始阅读的。阅读通常是一种让我头疼、需要努力的摄入信息行为,但我知道巴什拉的书反而会让我从工作中解脱出来、带给我不一样的思维。当我在九点多结束加班、回到暂居的房间时,打开手机阅读他的文字,我获得一种安逸。他的文字本身便饱含诗意,是一种弥散的而非凝练的理论,阅读体验像是放任自己在梦想与感性的海洋中畅游,泡在温润的水里,任由自己的思绪随之一同弥漫。对它的阅读方式应该是如书中介绍的方法一般去梦想,如果要以实用主义思维去对其分析或拆解,那么风味就会大打折扣。就如下面这一段所说:
在这样一种心灵状态中,人能够清楚地感到,逻辑上的对立面在其太强烈的光照下,能将任何半明半暗的本体论的可能性消除殆尽。只能以极柔和的触摸,在一种微光与半明半暗的辩证关系中,去追踪试图存在的人性的一切苗头。(P143)
不过在结束这场漫游后,我还是打算以分析的方法记录一下梗概,方便自己回顾,也为他人提供一些内容的参考:
分章概述
第一章 追寻梦想的梦想词的梦想者
第一章阐述了词语之中存在的梦想。词汇能令人产生无限遐想,譬如“温暖的火”、“沉静的水”,诗人能从词句之中挖掘出含义,并将这种形象带给读者,使读者们也开始梦想。法语是一种具有阴阳性的语言,而梦想、内心的宁静总是阴性的词汇。当含义为阴性的词汇,在词性上竟然是阳性时,会让人感到别扭。
第五章有一个引用的注解是很好的解释:
“有一些词是‘言语的贝壳’……在聆听某些词的时候,正像孩子在贝壳中聆听到大海,词的幻想者听到了一个幻想世界的喧哗。”(P265 脚注3)
《梦想的诗学》(La Poétique de la Rêverie)这个书名是建立在这样一组词上的:阳性的梦(le rêver)和阴性的梦想(la rêverie)。阳性的梦指的是夜梦,人在夜间所作的混乱纷繁、不包含人之意志、不受控制的梦。本书不讨论夜梦,而是讨论梦想。梦想是白天的梦,即白日梦,是人主动去梦想。人总是在孤独中产生梦想,人在梦想中是安宁且舒适的。
第二章 追寻梦想的梦想“阿尼姆斯”与“阿尼玛”
第二章基于第一章“对词语的梦想”的基础上,描述了Animus(阿尼姆斯/阳性)与Anima(阿尼玛/阴性)两种属性。并非是“Animus对应男性、Anima对应女性”这样简单的对应关系,这一对属性与性别没有关联,而是每个人之中都包含了Animus和Anima。Animus是阳性的,人立足于社会所需要的那些理性、思考、行动力、策划、方案均属于Animus的范畴;而Anima则是人类最初的本能中所带有的阴性的安宁,一切的安宁都属于Anima的领域。本书主要着重于讨论Anima,因此对Animus没有太多论述,只在与Anima进行区分时才顺带说两句,整体显得有点嫌弃Animus,但这不是巴什拉的本意。他在书的结尾提到,希望未来能写一本专门论述Animus的书,不过似乎没能写出来……
提及这种阴阳性的概念后,他讨论了炼金术中对物质赋予阴阳的行为。炼金术就是一种对物质与词语的梦想,太阳与火焰代表着男性及国王,而月亮与水则代表女性及王后,物质在反应中结合,这便是一种对阴阳调和的梦想,体现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以及追求真理的思路。
这一章也提及了伴侣关系(只讨论了男女模式的关系),他提出了伴侣双方的Animus与Anima的多重关系:男性所追求的女性是他自身的Anima的投影,女性所追求的男性是她自身Animus的投影。在一对爱侣之间,他们将自己的另一侧互相投射在对方身上,在伴侣身上进行梦想。
梦想以激情体验未来,它使其激情的对象理想化。理想中的女性存在倾听着充满激情的男星梦想者。女性的梦想者使理想化的男人吐露其爱情。
无疑,文化的压力目前已到达诸如“女权主义”加强了妇女的“阿尼姆斯一样的程度”……对于女权主义毁坏了女性特征,人们谈论得够多了。但是,还得再提一次,假若要赋予梦想其基本特征,假若要把梦想看作一种状态,一种无需拟定方案的现在状态,那就必须承认梦想将任何梦想者,男人抑或女人,从要求权利的世界中解放出来。梦想与任何权利要求背道而驰。在纯粹的梦想里,在使梦想者回归于他安静孤独的梦想时,任何男人抑或女人,从“梦想的斜坡”往下走,一直往下走时,都能找到他在深层的“阿尼玛”中的安宁。这是在往下走而非往下坠落。在这一未确定的深处是阴性安宁的天地。正是在这无忧无虑、无野心、无方案计划的阴性安宁中,我们得到了具体的安宁,使我们的全部存在得到休息的安宁。……“白昼注定要使我们在黑夜之后恢复安宁,换言之,清醒的白日梦想注定要使我们在夜梦之后恢复安宁。”
……
相反,白日的梦想却享有一种清醒的平静。即使它染上忧郁的色彩,那也是令人安宁的忧郁,使我们的安宁延续不断的、和蔼可亲的忧郁。
(P81)
虽然上一段提到了“女权主义破坏了女性特征”,但我觉得他并非是反对女权主义(得多读点他的其他作品,才能确定他在这方面的理念),而是一种跳脱出权力关系思维、客观看待男性及女性的视角。在他看来,一个人应当是将自己的Animus与Anima调和平衡的,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应当具有自己的气质,有过多的Animus或Anima都只是走向某种极端:
从“阿尼姆斯”与“阿尼玛”的主题来看,如果他走向分裂的极端,那他将会成为人的一种怪相。这样的怪相确实存在:有某些过分男人气的男人和女人,也有某些过分女人气的男人和女人。美好的天性趋向于在同一心灵中取消这些过分情况,以促使“阿尼姆斯”及“阿尼玛”的力量亲切交往。(P119)
第三章 向往童年的梦想
一种潜在的童年存在于我们身心中。当我们更多地在梦想中而不是在现实中重寻童年时,我们再次体验到它的可能性。我们梦想着这一童年本可以成为的一切,我们梦想着历史及传说的极限。(P129)
可能是时代的缘故,我比较难与这章的内容产生共鸣。第三章描述了大量的乡村小宅、森林等形象,但我从小在城市长大,不曾拥有乡间小屋和田野里的回忆,只记得狭小的居民楼与工厂区那融化的塑胶气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不存在于城市里。根据工作后同事们分享给我的转述,我才能窥见乡村生活的一角。他们的确从自然中得到了许多乐趣,也更清楚人是如何踏在土地上通过劳作去实实在在地生活的。然而,尽管我不曾真实地体验过他们的生活,在读书的时候,我也总是偏爱那些讲述种植、手工品、森林游戏的片段,或许这也证明了对于自然的向往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
不过,说到可能性的问题上,我本人就深有感触了。童年存在着无限可能性,在被社会的要求观测之前,它还未坍缩到唯一的可能性上,所以孩子们可以自由地梦想。小学的我们便会梦想自己会成为宇航员、画家、科学家等职业。直到高中的时候,我还没决定好自己想做什么,只是模糊地对我的未来存在梦想,通过梦想“等到毕业之后,我会有大把时间折腾爱好,不会再有作业挡在我面前”,以获得心灵的安宁和存在的安稳。但在进入大学、被归入一个专业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成年人只能在一个方向上深造,我的诸多梦想已经化为不可能,只剩下了唯一的可能性。那时候的我抑郁了,按照本书的思维,或许就是当时的我失去了梦想的能力、存在的基础被打破了吧。
第四章 梦想者的“我思”
在思考精神分析的教导时,人们已清楚地感到又被送回到表面的区域,送回到社会化的区域。何况,他面对的是奇怪的悖论。当病人陈述他梦中稀奇古怪的曲折变化后,当他强调他的夜生活中的某些事件所具有的出人意料的特点后,精神分析学家凭借渊博的学养可能对他说:“这一切我都知道,我都理解,果然不出我所料。你与其他的人是同样的。尽管你梦中出现种种错乱,你并没有独特生活的特权。”
于是,正是精神分析学家负责宣布做梦人的“我思”:“他夜里做梦,因此他夜里存在。他和所有人一样做梦,因此,他像所有的人一样存在。”
“在夜里,他自以为是自己,而其实他是无关紧要的人。”
无关紧要的人?或者也许是——人的存在的灾难——随便什么东西。
随便什么东西吗?某种热血的冲动,某种失去机能克制的过剩的荷尔蒙。
从随便什么时候而来的随便什么东西吗?过去的奶瓶中装的过于稀少的奶。
(P192)
区分夜梦与白日梦的一章。夜梦之中,不包含人的主观意识,只是一片混乱。但白日梦则是人的主观行为,人生存于他们的梦想中。
是我不太能理解、读得比较痛苦的一章,就暂且不多说什么了。如果之后有空重读,或者等我读了笛卡尔的“我思”,再来补充。
第五章 梦想与宇宙
这一章是完美的收官,让我把先前的痛苦一扫而空。在这一章中,梦想者的触须伸向宇宙,自然万物都成为其梦想中的存在。现象学认为一切都是人所见的现象,既然一切都必须经过“人类的认知”这一道工序,那么万事万物都逃不脱人的主观意识。既然一切认识都是主观的,何不干脆大胆地梦想?远古的神话便是人对自然梦想后的产物,一切都是围绕着人的存在,人通过梦想与宇宙融为一体。
的确,在文明出现以前,世界曾做过许多梦。神话从大地走出,神话开放了大地,为的是大地能以其湖水的眼睛注视天空。崇高的命运从深渊升起。于是,神话立即发现了人的声音,以他的梦,梦想者世界的人的声音。人表述大地、天空及水。人是这宏观人类即地球巨大躯体的言语。在原始的宇宙梦想中,世界是人的躯体、人的目光、人的气息和人的声音。(P245)
孩子长成了成人便不再做梦,文明脱离了童年又何尝不是如此?若是用理性去破除了神话与信仰,人类的安适感应该到哪里去寻找呢?梦想的诗学便是一种解决方法。诗是以语言表达丰富情感的文学体裁,按照实用的角度去看,诗是一种无用之物。它不能喂饱人的肚皮,不能给人带来居所和其他一切需要的物质,但哪怕是不解风情的人,在酒足饭饱之余,听到他人在炉火边吟诗,也将会心一笑,不再戳破它的“无用”。当你读诗,便是在主动地梦想,让诗人把形象带给你、在你心中激起共鸣,让你与宇宙融为一体。在梦想的瞬间,你的体验超脱了物质的枷锁。你可以坐在办公室里,却同时在梦想的家园里。要梦想,要主动地去做白日梦。
人类刚进入一个新的成熟期,因此想象应为意志力提供服务,应唤醒意志进入全新的展望。正因如此,梦想者不能满足于通常的幻想。假若人能在抛开一本刚结束的书,又立即开始另一本,他该是多么喜悦啊!但在这样的意愿下,不应该陷入混淆类型的错误。对意志的梦想不应粗暴对待闲情逸趣的梦想,不应使之阳性化。(P278)
发散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联想到了很多东西,但难以归入以上的任何部分,便在这里发散一下吧。只是我根据自己所见联想到的一种思路,并不代表我是对的,仅供随便看看。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有一种看法更为着重前者,认为一切问题都是物质的问题,只要改善物质环境,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虽然解决物质问题可以解决绝大多数问题,但在我看来,还存在很多意识的问题,哪怕改善了物质条件,也无法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更不是说只要物质足够充裕,人就必然会快乐。指望物质能解决所有问题是不太现实的,在物质条件丰富的地区,仍然会诞生精神疾病。在物质问题难以解决的时候,意识也可以排解人的痛苦。从十几元的书本中,人可以获得不亚于百元娱乐活动的快乐;在高档酒店度过的秋日,未必比在公园的桂花树下静坐更为快乐。当生活无忧时,意识仍会感到无聊与痛苦;当生活困苦时,意识也仍能苦中作乐。需要努力去解决物质上的问题,但意识的问题同样需要引导,不能放弃这部分的工作,不能指望解决了物质的问题就万事大吉。
如果把话题缩小到意识及精神的领域,思考与感受又是一个岔路口。INZO有一首曲子叫做《Overthinker》,其中有一段采样出自出自Alan Watts Teaches Meditation (1992):
A person who thinks all the time has nothing to think about except thoughts. So, he loses touch with reality and lives in a world of illusions. By thoughts I mean specifically, chatter in the skull… Perpetual and compulsive repetition of words… of reckoning and calculating.
I’m not saying thinking is bad. Like everything else, it’s useful in moderation. A good servant, but a bad master – and all so called civilized peoples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crazy and self-destructive. Through excessive thinking, they have lost touch with reality.
Most of us would have rather money than tangible wealth… and a great occasion is somehow spoiled for us unless photographed… and to read about it the next day in the newspaper is oddly more fun for us than the original event. This is a disaster.
To get in touch with reality there is an art of meditation… It is the art of temporarily silencing the mind… of stopping the chatter in the skull. Of course you can’t force your mind to be silent. That would be like trying to smooth ripples in water with a flat iron. Water become cool and clear only when left alone.
翻译如下:
一个终日思考的人,除了思想以外,便想不到其他东西。他失去了与现实的接触,居于一个幻想中的世界里。我所说的思想,是特指“脑海里的喋喋不休(Chatter in the skull)”,即不间断地、强迫性地重复着预估与计算。
我并不是说思考是不好的。就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只要适度,思考是十分有用的。思考可以成为一个好的仆从,却是坏的主人。所有文明、教化的人类,正在日渐倾向疯狂与自我毁灭,因为,通过过度的思考,他们失去了与现实的接触。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比起真正的财富,更想要金钱。而一个伟大的时刻,如果没有被拍摄下来,对我们而言就如变质了一般。在第二天,当我们从报纸上读到这件事,又觉得这新闻比最初的事件有更多古怪的乐趣。这是一场灾难。
冥想的艺术便是为了与现实接触。那是一种关于如何暂时使意识安静的艺术,用来停止“脑海中的喋喋不休”。你当然不能强迫自己的意识保持安静,那就像是试图用熨斗来抹平水面的波纹一样。水只有在被放置不理的时候,才会是平静而无波澜的。
这段话否定了“沉浸于自己的幻想”的行为,但我认为这与《梦想的诗学》里所提到的“主动地梦想”是不同的。这段采样中提到的,是指人们把玩弄概念这件事变得日益复杂,以至于脱离了现实,比起真实的世界,更多地生存在概念之中。而《梦想的诗学》所提及的,则是恢复人与自然之连接的梦想。可以说,采样中的是Animus的繁杂计算,《梦想的诗学》则是Anima的放松与安宁。采样所给出的解决过度思考的方法,便是冥想,这同样是一种Anima的概念和行为。
采样中所说的过度思考(overthink),在巴什拉的体系中也有提及,就是与现象学相对的精神分析学家和心理学家们。他们致力于将梦想中的一切都找到现实中的对应,认定一切皆有理由,以理性去解构分析阴性的梦想,随后为每一个无逻辑的意象找到原因,从而“解决”它们。他们思考梦想,这或许就是一种过度思考。如果看到一件事的第一反应,是喋喋不休地在脑海中蹦出诸多评价信息,那么这虽然有助于思考,却无益于感受。
思考可以破解感受,因为思考本身就是对现实的解构,它对感受唯一能做的事便是解构。但这不代表思考高于感受,因为两种不同的语言在互相翻译的过程中,必然会损失部分信息。不能因为思考解构了感受,就认为解构后的结果是完整的,从而证明思考更为强大——这种一定要将两种能力比个高下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过度思考的体现。
在网络和生活上,我所感受到的是,思考是高尚的,而感受是低下的、柔弱的。一如“男性更为理智,女性更为感性,所以不能和女人讲道理”的怪异论调。如果要说阴柔的展现会被如此鄙视,除了当代的工业社会对人的效率要求,我认为父权体系也占了一部分缘由。
《神圣的欢爱》中提到,远古时的母系社会时期,人类更多的是伙伴关系,在进入父权社会后,才逐渐转变为今日的竞争关系。按照巴什拉的体系,这或许就是社会层面的由阴性转变到阳性吧。Animus的能力是为了生存的能力,为了建造大型灌溉系统、完成大型工程、让人类文明达到更高的高度,Animus的能力是必要的,一味追求内心安宁的Anima是做不到的。如果单纯放任Anima主导,人人都只追求快乐,那么所有的人类到今天都还只会生存在原始部落里,直到某一天,一场未知的伽马射线暴击中了地球,人类就此在对神明的困惑与惊恐中消亡吧。
但是,到了如今,当精神病在Animus的社会里越来越多,当阴柔被鄙视、人们被禁止阴柔时,Anima又成为了新的解决方法。说到底,获得安适才是人类的最终目的,打破本能的目的在于让本能更加舒适。如果今天的社会已经焦躁到让人难以忍受,那么继续互相倾轧也是没用的,得浇上一点阴柔的水。《神圣的欢爱》最后提到,越来越多的男性及女性都在觉醒,试图抵抗竞争关系主导的社会,回到伙伴关系。我也认为,在Animus奔跑到如此程度的当下,是时候多关注一些Anima了。
最后,以这段引用来作结尾吧:
知识每次取得具有建设性的抽象化后,其雄健性就有所增长。这种进行抽象化的行动与心理学著作的描述颇不相同。数学中抽象思想的组织能力很显然。正如尼采所谓:“在数学中……绝对知识纵情欢庆其佳节。”
热衷于理性思想的人能对非理性主义者所散步的烟雾无动于衷,后者试图以烟雾在紧密组合的概念闪耀出的光明周围散布怀疑。
烟与雾,这是阴性的反对。
(P71)